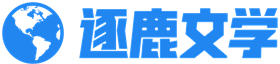新的一天,是在闹钟响起前的十几分钟,被窗外一只麻雀梳理羽毛的“簌簌”声吵醒的。
李文睁开眼,盯着天花板上因光线变化而缓缓移动的、细微的灰尘影子,眼神里没有了前一天的惊慌与疲惫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难明的平静。
恐惧并未消失。它像一条冬眠的毒蛇,盘踞在他灵魂的最深处,随时可能苏醒,给予他致命一击。但现在,一种新的、更强大的驱动力,暂时将这条毒蛇压制了下去。
【扮演法】。
这三个字,像一道光,照亮了他眼前那片被迷雾笼罩的、通往超凡世界的危险道路。它为李文提供了一套可以理解、可以执行的行动纲领,一个在疯狂边缘维持理智的“锚”。
他不再是一个被动承受一切的受害者,而是一个需要主动出击的“扮演者”。
他要扮演“收藏家”。
一个真正的收藏家,会如何对待自己的藏品?他不会因为藏品危险就将其束之高阁,任其蒙尘。恰恰相反,他会投入十二分的热情与专注,去研究它、解读它、理解它,最终,彻底地掌控它。
这既是“消化”力量的方法,也是他唯一能够自救的途径。
想通了这一点,李文感觉自己那紧绷了一整天的神经,终于得到了一丝舒缓。他从床上坐起,感觉身体虽然依旧疲惫,但精神上的重压却减轻了不少。
他像往常一样洗漱、吃早饭。在做这些事的时候,他有意识地训练着自己对那“超级感官”的控制力。他试着将注意力集中在牙刷的摩擦声上,而忽略掉水龙头内部水垢流动的杂音;他试着专注于面包的麦香,而屏蔽掉厨房角落里那袋垃圾散发出的、被分解成上百种不同气味的复杂信息。
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,像是在重新学习如何走路。但他惊喜地发现,每一次成功的专注,都会让他的精神感到一丝轻松。这似乎也印证了【扮演法】的有效性——“专注”,本身就是“收藏家”所必备的品质之一。
当他再次踏入图书馆时,他的状态已经比昨天好了许多。虽然依旧无法完全屏蔽掉那些过载的信息,但至少不会再让他感到头痛欲裂了。
“小李,今天来挺早啊。”王叔正端着一个巨大的搪瓷茶缸,慢悠悠地从走廊那头晃过来。
“王叔早。”李文点点头,微笑着打了个招呼。
凭借着敏锐的感官,他甚至能从王叔略显发飘的脚步和眼底的血丝中,判断出他昨晚大概率是看了一宿的球赛,而且他支持的球队很可能输了。这种于无声处洞察细节的能力,让他产生了一种奇妙的“全知感”。
他走进古籍修复室,反锁上门,然后从自己的私人保险柜里,取出了那本《静海市地方水文异闻录》。
他没有立刻开始阅读,而是先将其郑重地放在了工作台上。然后,他走到墙角,从那堆无人问津的旧书中,将那本通体漆黑的无字之书也取了出来。
他将两件“藏品”并排放在一起。
一件,是来自禁忌之地的知识载体。
另一件,则是一切的源头,那枚【梦境残晶】的“巢穴”。
他深吸一口气,正式开始了他的“扮演”。
他戴上最专业的手套,拿起放大镜和各种精密工具,开始对这两件藏品进行最细致的“编目”和“研究”。他不再将它们视为单纯的危险品,而是当成了自己职业生涯中遇到的、最珍贵、最富挑战性的古籍。
他首先研究的是那本黑皮书。
他测量了它的尺寸、重量,用高倍放大镜观察皮革的纹理,试图分析其材质。他甚至用沾着蒸馏水的棉签,在封皮一个极其隐蔽的角落轻轻擦拭,然后将棉签封存,准备有机会送到专业的实验室去化验。
接着是里面的空白书页。他记录下纸张的柔韧度、色泽、以及对光线的反射率。他再次找到了那个嵌着【梦境残晶】的夹缝,这一次,他没有恐惧,而是以一个研究者的心态,仔细地观察着水晶与书页的结合方式。
他发现,那枚水晶并非被简单地夹在里面,书页的纤维,似乎以一种极其细微的方式,与水晶的边缘“生长”在了一起。它们仿佛是一个共生体。
这个发现让他不寒而栗,但也让他对这件“藏品”的理解更深了一分。
做完这一切,他才将注意力转移到那本《静海市地方水文异闻录》上。
他开始逐字逐句地精读。
有了【扮演法】的指引,他发现自己在阅读这本书时,不再像昨天那样感到头皮发麻,而是以一种更加客观、更加抽离的角度,去分析和记录书中的信息。
他准备了一个全新的工作笔记,将书中提到的每一个“异闻”,都与他所知的、真实的历史事件进行对照。
【明崇祯九年,静海大旱,赤地千里。书中记载为‘地底火龙翻身’,征兆为‘城西古井喷出黑烟三日’。】
李文立刻在电脑上查阅了《静海县志》。县志中确实记载了崇祯九年的那场特大旱灾,但对于“古井喷烟”这种怪力乱神之事,却只字未提。
他又继续往下看。
【清康熙十三年,风雨大作,连月不止,江水倒灌,淹没良田万顷。书中记载为‘江中旧神苏醒’,征兆为‘渔夫于江心捞起带人脸之怪鱼’。】
他再次查阅资料,同样,史料中只记载了那场罕见的洪灾,对于“人面怪鱼”这种传说,没有任何官方记录。
这本书,就像是一部“里历史”。它与真实的历史并行不悖,却又在每一个关键的节点上,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、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的解释。
李文沉浸在这种考据和对比之中,几乎忘记了时间的流逝。这种专注而深入的研究,正是“收藏家”的本职工作。他能感觉到,随着自己对这些禁忌知识的理解越来越深,他那躁动不安的精神,正在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缓缓地抚平。
那些过于敏锐的感官,似乎也变得更加“听话”了。他可以更加自如地控制自己的注意力,将那些无用的杂音和信息屏蔽在外。
这让他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了【扮演法】的好处。
“咚咚咚。”
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他的研究。
李文立刻将两本书收好,锁进保险柜,然后才起身开门。
门口站着的是实习生小赵,他手里捧着几份文件,脸上带着一丝焦急。
“李老师,这份文件需要编目科的陈老师签字,但我找了一圈都没找到他,打他电话也没人接,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?”
“老陈?”李文愣了一下,“他今天没来上班吗?”
“没来,”小赵摇摇头,“早上就没见着人,王主任还念叨着说他不够意思,请假也不提前打个招呼。我们都以为他睡过头了,可这都快下午了,电话也打不通,就有点奇怪了。”
李文的心里,没来由地“咯噔”一下。
编目科的老陈,他有印象。一个五十岁出头、性格有点孤僻的老好人,平时沉默寡言,工作却极其认真负责。他是馆里少数几个能跟得上李文工作节奏的人之一。像他这样的人,绝不可能无故旷工。
而且,李文清晰地记得,昨天王叔推进来的那车捐赠书籍,在送到他这里之前,就是由编目科负责初步清点和登记的。
也就是说,老陈,是除了他之外,第一个接触到那本黑皮书的人。
这个念头,像一颗投入湖中的石子,在李文的心里激起了一圈冰冷的涟漪。
“我知道了,你先把文件放这儿吧,我等下也帮忙找找看。”李文不动声色地接过文件。
等小赵离开后,李文再也无法静下心来研究那本《异闻录》。他立刻登录了图书馆的内部系统,调出了那批捐赠书籍的入库清单。
清单的电子扫描件很快就显示了出来,上面是老陈那熟悉的、一丝不苟的字迹。李文一目十行地扫下去,他的目光在寻找着任何与那本黑皮书相关的描述。
清单上记录了《莎士比亚集》、《社会契约论》等等,一共三十七本书。
但是,没有那本黑皮书。
李文皱起了眉头。难道是老陈漏掉了?这不像他的风格。
他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,这一次,他注意到了一个极其微小的细节。
在清单的末尾,第37项记录的下面,有一小片不太明显的、被涂改液覆盖过的痕迹。在普通人看来,这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小错误。
但在李文那被强化过的、堪比显微镜的视力下,他能清晰地看到,在薄薄的涂改液层之下,隐约透出几个字迹的轮廓。
他立刻从工具架上取来一小瓶专用的化学试剂和一根棉签。这是他们修复师用来处理一些被污染稿件的专业工具。他小心翼翼地,用棉签沾着试剂,在那片涂改痕迹上轻轻地擦拭。
刺鼻的气味弥漫开来,白色的涂改液层,开始一点点地变软、溶解,露出了下面被遮盖住的、原始的墨水字迹。
那是一行被划掉了的、潦草的字:
【第38项:黑皮无字石书(?),材质不明,极重,疑似……】
字迹到这里就断了,后面是一个被墨水涂成一团的、看不清的词。而紧接着,就是这行字被粗暴地划掉,并用涂改液覆盖的痕迹。
李文的心,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。
老陈不但接触过那本书,而且发现了它的异常!他甚至准确地判断出它的材质不像纸,而像“石书”。那个潦草的笔迹和最后的涂抹,清晰地表明了他当时内心的震惊与不确定。
但他为什么要把这条记录删掉?又为什么会在第二天就离奇地失踪?
一个可怕的猜想,在李文的脑海中不受控制地浮现出来。
他立刻关掉电脑,快步走出了修复室,向着位于二楼的编目科办公室走去。
现在是下午工作时间,编目科里人不多,大家都在埋头处理着堆积如山的书籍。看到李文进来,都有些意外。
“小李?稀客啊,有事?”一个和老陈关系不错的大姐笑着问道。
“王姐,我来找找陈老师,有点工作上的事想请教他。”李文装作若无其事地说道。
“别提了,老陈今天一天都没影儿,手机也关机,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?”王姐担忧地说道。
李文没有接话,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办公室角落里那个属于老陈的座位。
桌子收拾得很整齐,符合老陈一贯的风格。水杯、笔筒、老花镜……一切看起来都正常无比。
但在李文的“视野”里,那里却笼罩着一层若有若无的、极其淡薄的“异常感”。
他缓缓地走了过去,装作在看老陈桌上的文件,手指却状似无意地,轻轻拂过了老陈那张用了十几年的旧木椅子。
就在指尖触碰到椅背的瞬间,一股微弱但清晰的、与他触摸【梦境残晶】时同源的冰凉感,一闪而逝。
紧接着,一个破碎的、一闪而过的画面,突兀地闯入了他的脑海——
那是在一个昏暗的房间里,老陈正惊恐地看着自己的双手,而他的十根手指,正在一点一点地、如同风干的泥土般,龟裂、剥落,化为灰黑色的粉尘。
画面瞬间消失。
李文的身体猛地一震,脸色在一瞬间变得煞白。
他看到的,是老陈失踪前,最后留下的“记忆残响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