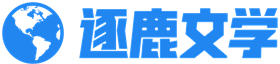第8章
王姐那句“你敢不敢单独负责”,像根钉子,把孙晓雅死死钉在那儿,整个车间的人都看着。空气好像不流动了,只有旧吊扇在那儿嗡嗡响,窗外偶尔有摩托车开过去的声音。晓雅觉得有两道很扎人的目光从阿珍阿丽那边射过来,带着吃惊和不爽。她咽了口口水,喉咙发干,手指头不自觉地搓着衣角,这是她从东北带过来的习惯,一紧张就这样,好像指头上还有以前在厂里数钱时那种潮乎乎的感觉。但下一秒,她抬头对上王姐那双藏着期待的眼睛,深吸一口气,把腰板挺直了,说:“我敢。”
王姐脸上没啥表情,只轻轻点了一下头,把一厚摞订单资料和客户给的样品布料扔到工作台上。“要求全在这里面。三天时间,从看懂要求、出图纸到打出合格的初版,你一个人搞定。如果用料超了预算,或者东西客户不满意,”她停了一下,眼睛扫了一圈车间,“亏的钱从你工资里扣,扣不完,你就给我白干活,直到还清。”这话与其说是说给晓雅听的,不如是说给所有人立的规矩,冷冰冰的,一点人情味都没有。可是,她转身要走的时候,手指很快地在布料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点了一下,那儿有个用差不多颜色的线绣的一个小字母“B”。这动作快得像错觉,只有死死盯着王姐的晓雅看见了。
晓雅马上懂了,这是王姐偷偷给的提示。客户明面上要的是A版型,但这个“B”可能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,或者有别的特殊要求。王姐帮忙帮得这么隐蔽,又这么险,把指点藏在考验底下,好像是在说:路我可以指给你,但坑还得你自己爬。
麻烦马上就来了。客户要的是一种复杂的双面提花布,对纱线的松紧、针脚怎么配合要求特别高。晓雅一头扎进图纸和机器里,反复算、反复调。另外两个女孩,阿珍和阿丽,显然看不惯她这个“外地人”,尤其是她们瞧不上的“东北人”接这么重要的活儿。她们先是“不小心”弄乱晓雅分好的彩色纱线,又在她调机器的时候,故意在旁边用方言大声说“有些人没那个本事还要拖累全厂”,想搅乱她的心思。晓雅只当没听见,默默把纱线重新分好,把重要的参数用只有自己才懂的符号记在小本子上。这是在东北厂里养成的习惯,怕手艺被人轻易学去。
真正的使坏发生在第二天半夜。晓雅顺着“B”的提示,终于发现客户其实是想要在很薄的底布上做出凸起来的花纹,这得改平常的走针顺序和换线的节奏。她刚摸出点门道,离开一会儿去喝口水,回来就发现她刚调好的机器被人按回了初始状态,所有数据都没了。车间里只有阿珍在远处低着头缝边,好像什么都不知道。
晓雅站在冰冷的机器前面,火气一下子冲到头。她几乎能肯定是阿珍干的。这一刻,她不是没想过冲过去吵一架,但东北那种直来直去的脾气,被来南方这几个阵子学会的忍劲压了下去。她想起王姐“不准打听别人的版、不准私下接活”的规矩,也想起自己刚来时被人说“粗手粗脚”。吵架只会浪费时间,正好坐实了“东北人冲动坏事”的偏见。她咬紧牙,没吭声,靠着记忆和小本上的符号,慢慢把参数重新输进去。那个晚上,车间里只有机器低沉的嗡嗡声和她像钉在那儿的身影。失败,重来,再失败,再调整。手指上的旧伤被针柄又磨破了,血珠渗出来染红了纱线,她只是简单贴了块胶布,继续干。
第三天一大早,王姐像往常一样来得特别早。她看见晓雅脸煞白但眼睛发亮地站在机器前,脚边是一小堆试坏了的废布头。她没问做得怎么样,直接走到晓雅旁边,扔给她一个旧铝饭盒,里面是热乎乎的菜肉大馄饨。“吃。别死在我这儿。”语气还是那么硬,但这举动有种江湖式的关心。她看着晓雅大口吃着,忽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:“我以前在广东大厂,带出过十几个徒弟。最让我得意那个,偷了我所有花样设计,带着客户自己出去开了厂。”
晓雅嚼馄饨的速度慢了下来。王姐眼睛看着窗外渐渐热闹起来的街道,声音平平的,但带着深深的累和一丝没被时间磨平的痛:“那时候我才明白,手艺是死的,人心是活的。教人手艺,也得防着人心。”所以她数钱时才有那股子市井的江湖气,那是她保护自己劳动最直接的办法;所以她定下那么严的规矩,对学徒,尤其是外地人,看得特别紧;所以她把技术上的指点藏在这种冷酷的考验下面。她可能也想有人能继承手艺,但更怕再被背后捅一刀。这个细节让王姐这个人一下子复杂了起来,她的严厉和一丝不苟不是天生的,是受过伤后长出来的硬壳。
最后一天下午,客户派人来验货。来的是个穿着讲究、表情很严肃的中年男人。阿珍和阿丽抱着胳膊站在不远的地方,等着看笑话。王姐坐在办公室里,没出来,好像这事跟她没关系。
晓雅把打出来的初版样衣平平地铺在验货台上。中年男人拿起放大镜,仔细看每一个地方:花纹对得齐不齐,线脚匀不匀,背面干净不干净……他特别留意那个暗号“B”指的特殊立体花纹区域。看了好久,他绷着的脸总算有了一点笑模样:“不错。尤其是这个立体效果,处理得很巧,跟我们想的一样,甚至更好。王师傅手下真是有能人。”
一直绷紧神经的晓雅,听到这话,腿一软,赶紧用手撑住台子。王姐不知什么时候走了出来,脸上还是淡淡的,只对客户点了点头:“应该的。”但当她目光扫过晓雅时,眼睛最里面飞快地闪过一点很难察觉的赞许和放松。
客户走了以后,车间里静得奇怪。王姐走到晓雅面前,掏出一把零钱,利索地数出五十块钱奖金,和当月工资一起拍在晓雅手里:“这是奖金。下个月起,你工资涨到三百五。”她停了一下,声音压低了些,只让晓雅一个人听到,“那台进口机器,以后主要归你管。”
晓雅抓着那叠有点潮乎乎的钱,手指头不自觉地蘸了下口水,熟练地数了数,心里什么滋味都有。她赢了这一仗,得到了认可和机会。但她也很清楚地看到,王姐身后,阿珍和阿丽的脸色变得特别难看,眼神里不再是看不起,变成了嫉妒和怨恨。
王姐转身叫杂工去搬新来的纱线,她数钱时那种有点俗气的习惯动作,和她检查纱线质量时那种特别较真的专业劲儿,放在一起很别扭,但又同时存在。这暗示着她复杂的过去:她可能是从底层爬上来的,靠着过硬的技术和一股狠劲混出来,但身上还留着草莽的痕迹。她把对技术的纯粹追求藏在冷酷的规矩和试探下面,心里可能藏着不想说的苦楚和孤单。
晓雅知道,自己只是在这片精密又冷漠的工厂丛林里,暂时喘了口气。真想站稳脚跟,还早着呢。而王姐那张冷脸后面,到底还藏着什么故事,她才刚刚看到一条缝。南北的差异、技术的传授、人心的好坏,在这间小小的打版店里,搅和成一幅更复杂的画,等着下一次展开。
那天晚上,晓雅给赵志刚写了第二封信,这次她留下了详细地址。她在信最后写:“这里能学到真本事,但南方的水,好像比我想的要深。”然后她拿出这个月攒下的一点钱,又一次不自觉地舔湿手指头,仔细数了两遍,把信纸折好,塞到了枕头底下。
阁楼窗外,濮院的晚上还是灯火通明,摩托车呼呼地跑,但这个南方小镇在晓雅眼里,不再只是充满希望的地方了,它的每一道纹理里都缠着机会、偏见、高超的技术,还有藏在精密机器下面、没人清楚的暗流。她的战斗,才刚开了个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