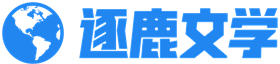初冬的冷风裹着细雨敲在鼎盛办公楼的玻璃上,林砚站在窗前,手里攥着李薇刚送来的财务报表,指腹反复摩挲着“资金缺口50万”那行字。研发组急需的检测设备要18万,拓展外地经销商的差旅费和样品费得12万,下个月的员工社保和原材料采购还得20万——几笔钱加起来,像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他心上。
“林总,要不咱们再跟银行试试?”李薇站在旁边,声音带着几分犹豫,“虽然上次贷款刚还完,但咱们现在有新订单,说不定银行愿意再批点。”
林砚摇了摇头,转身坐在沙发上:“我昨天已经问过了,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审批至少要两个月,咱们等不起。”他想起早上接到的匿名电话,对方自称是“李彪的朋友”,说能借50万,月息15%,用厂区的老厂房做抵押——那语气里的威胁,像根刺扎在心里。
“高利贷绝对不能碰。”林砚的声音很坚定,拿起桌上的《道德经》,翻到“善战者不怒,善胜敌者不与”那一页,“借高利贷就像喝毒药解渴,现在看着能填缺口,下个月利息就滚到7.5万,用不了半年,咱们连厂房都得赔进去。”
李薇点点头,却还是愁眉不展:“可除了银行和高利贷,咱们还能去哪找钱?总不能让研发组停了,或者不拓外地市场吧?”
林砚没说话,手指在报表上轻轻敲着。他想起刚接手鼎盛时,厂里连工资都发不出来,最后靠抵押房子才撑过来,现在公司刚有起色,绝不能再走回头路。“走,跟我去厂区转转。”林砚突然起身,抓起外套就往外走,“说不定能找到解决办法。”
雨已经停了,厂区的水泥地上积着浅浅的水洼。林砚绕着生产车间走了一圈,最后停在西北角的老厂房前。这厂房建于90年代,红砖墙爬满了青苔,锈迹斑斑的铁门紧闭着,透过窗户能看到里面落满灰尘的老式机床——自从新车间建成后,这里就闲置了三年,成了堆放杂物的地方。
“林总,您看这老厂房干嘛?”李薇跟着停下来,不解地问,“里面除了些旧设备,啥都没有,之前有人想租来当仓库,您嫌租金太低没同意。”
林砚盯着老厂房的红砖墙,突然眼睛一亮:“没同意租当仓库,是因为它能发挥更大的价值。”他推开虚掩的铁门,走进去指着那些老式机床:“你看这些机床,虽然不能生产了,但带着90年代的工业痕迹,现在文创行业不是流行‘工业风’吗?咱们把这里改造成文创工作室,租给做设计、搞展览的公司,说不定比当仓库赚得多。”
李薇愣了愣,随即反应过来:“您是说,把闲置厂房改成文创空间?这能行吗?”
“行不行,得先调研。”林砚拿出手机,对着厂房拍了几张照片,“老周之前参与过这厂房的建设,他最清楚这里的结构;陈默现在在市场部,让他打听下本地文创公司的需求——咱们得弄明白,文创公司需要什么样的场地,愿意出多少租金,再决定怎么改。”
当天下午,林砚就把老周和陈默叫到了办公室。老周拿着泛黄的厂房图纸,指着上面的标注说:“这厂房占地800㎡,中间是大车间,两边有四个小隔间,承重和采光都没问题,就是屋顶得做防水,墙也得重新刷一遍。”
陈默则带来了调研结果:“本地有十几家文创公司,大部分都在写字楼里办公,租金贵还没特色。我联系了一家叫‘青蓝文创’的公司,老板周晓说,他们一直在找有‘历史感’的场地,用来做设计工作室和小型展览,要是咱们的老厂房合适,他们愿意长期租。”
“太好了!”林砚一拍桌子,把手机里的厂房照片递给两人,“老周,你整理一份《老厂房文创改造可行性报告》,把厂房的历史、结构、可改造的空间都写清楚,尤其是那三台老式机床,要突出它们的‘工业特色’;陈默,你联系周晓,就说我想跟他见面聊聊,地点定在咱们厂里的小会议室,让他亲眼看看厂房。”
三天后,周晓准时来到鼎盛。他穿着休闲的牛仔外套,戴着黑框眼镜,一进会议室就盯着墙上的老厂房照片:“林总,您这厂房的底子是真不错,红砖墙、老机床,正是我们想要的‘工业风’。”
林砚笑着递过报告:“周总,您先看看这份报告,里面写了厂房的详细情况。我们的想法是,不做大规模改造,保留原有结构和老机床,只做防水、刷墙和电路改造,这样既能保持工业特色,又能控制成本。”
周晓翻着报告,时不时点头,看到“可划分10个独立工作室,预留200㎡做展览区”的规划时,眼睛亮了:“这个规划很合理,我们正好需要独立工作室给设计师用,展览区还能办小型沙龙,吸引客户。”
“那咱们就聊聊合作方式。”林砚身体微微前倾,语气诚恳,“您做文创需要有特色的场地,我们有闲置厂房却缺资金,这是‘各取所需’的事,我不想只收固定租金,想跟您做长期共赢的合作。”
周晓放下报告,饶有兴致地问:“哦?林总想怎么合作?”
“我有三个想法。”林砚伸出手指,一一说道,“第一,改造费用由贵公司承担,我们以场地入股,占30%的利润分成——毕竟改造后场地增值了,您的项目也能更有竞争力;第二,租期定5年,前两年租金每月3万,从第三年开始,每年按10%递增,租金按季度支付;第三,首季度免租,给您留出改造和招租的时间。”
周晓听完,手指在桌上敲了敲:“场地入股占30%利润分成,这个比例没问题,但改造费用我们全额承担,压力有点大。”他顿了顿,接着说:“我算了下,防水、刷墙、改电路,再加上简单装修,至少要50万,要是鼎盛能承担20%的改造费,我马上同意这个合作框架。”
林砚没立刻回答,转头看向老周。老周会意,接过话头:“周总,改造费50万确实不少,但这厂房的维护一直是我们在做,去年刚换了水管,今年年初又检修了电路,您只需要做防水和装修,实际费用大概40万。而且我们可以承担屋顶防水的3万费用,算是我们的诚意。”
周晓眼睛一亮:“要是能少13万,那没问题。”他拿起笔,在合作框架上签了自己的名字,“我回去跟团队确认下,一周后咱们签正式合同,争取下个月就开始改造。”
送走周晓,李薇激动地说:“林总,这合作成了,咱们每月至少多3万收入,年底还有利润分成,资金缺口总算有着落了!”
林砚点点头,却没放松警惕:“合作刚定框架,还没到高兴的时候。老鬼那边传来消息,赵坤的同伙在打听咱们厂房改造的事,说不定想从中作梗,咱们得提前防备。”
正说着,老鬼的电话打了过来,声音里带着急促:“头,我看到赵坤的小弟王虎,在老厂房附近转悠,还跟看门的老张打听改造的事,好像想在改造时搞破坏。”
林砚皱了皱眉,沉声道:“你继续盯着王虎,有情况随时告诉我。另外,让老张多留意厂区的陌生人,尤其是老厂房附近,晚上加派两个人巡逻——咱们不能让赵坤的人坏了咱们的事。”
挂了电话,林砚看着窗外的老厂房,心里清楚:盘活老厂房只是第一步,接下来还有改造、招租、应对赵坤同伙的破坏,每一步都不能出错。但他有信心——就像《管子》里说的“审其所好恶,则其长短可知也”,他们摸准了文创公司的需求,找对了合作方式,只要守住“共赢”的底线,就一定能把这件事做成。
第二天早上,林砚在管理层会议上宣布了合作进展。刘强拍着桌子说:“林总,您这招太妙了!既盘活了闲置厂房,又解决了资金问题,以后咱们研发组不用愁设备了!”
“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。”林砚笑着说,“老周整理的报告详细,陈默调研的需求准确,李薇把控着财务风险,还有大家一起盯着赵坤的人——咱们是团队,只有齐心协力,才能把鼎盛做得更好。”
会议结束后,林砚回到办公室,拿起桌上的《论语》,翻到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那一页。他想起跟周晓洽谈时的场景,要是只想着自己赚钱,不肯让利,合作也成不了。做生意和做人一样,只有替别人着想,才能实现真正的共赢。
这时,陈默敲门进来,手里拿着一份《外地经销商调研表》:“林总,这是我整理的外地经销商信息,北方有三家经销商对咱们的耐低温零件感兴趣,想下周来考察。”
林砚接过调研表,看到上面详细记录着经销商的规模、需求和合作意向,满意地点点头:“好,你跟李薇对接下,安排好考察路线,顺便把咱们厂房改造的事跟他们提提——让他们知道,鼎盛不仅能生产好零件,还在拓展新业务,实力越来越强。”
陈默点点头,转身离开时,林砚又叮嘱道:“跟经销商沟通时,要真诚,别夸大其词——《论语》里说‘言必信,行必果’,咱们要靠实力和诚信赢得合作,不是靠嘴说。”
看着陈默的背影,林砚拿起笔,在笔记本上写下“计划”:推进老厂房合作签约、接待外地经销商、加强厂区安保——每一项都清晰明了。他知道,接下来的日子会很忙,但只要方向对了,再忙也值得。
夕阳透过窗户,洒在笔记本上,“共赢”两个字被镀上了一层金边。林砚看着那两个字,嘴角露出笑容——鼎盛的未来,不仅有零件生产,还有文创合作、外地市场,这条路虽然难走,但只要一步一个脚印,就一定能走得稳、走得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