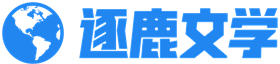简介
主角是沈砚陈峰的小说《谍影沉城:1941上海暗战》是由作者“喜欢姜荆叶的幽若谷”创作的抗战谍战著作,目前完结,更新了116640字。
谍影沉城:1941上海暗战小说章节免费试读
第18章:日军投降的预兆
1945年的夏天,上海像个被蒸透的蒸笼。六月的蝉鸣刚歇,七月的热浪又裹着潮湿的水汽扑在脸上,弄堂里的煤炉冒着黑烟,混着日军巡逻车的引擎声,织成一张沉闷的网。可这沉闷里,又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松动——自五月德国宣布投降的消息通过地下电台传到上海后,街头巷尾的空气里,就多了点不一样的味道。
沈砚之坐在“同和裁缝铺”的里间,指尖捏着一张皱巴巴的报纸,报纸上是日军控制的报社刊登的“大东亚共荣圈进展”,可他真正要看的,是夹在报纸缝里的一张小纸条——那是地下党联络员从重庆发来的密报,上面用暗号写着:“西线已平,东线孤木,秋前或有终局。”
“秋前……”沈砚之把纸条凑到油灯下烧了,灰烬顺着风飘进墙角的痰盂,“也就是说,日本撑不了多久了。”
苏清媛正在缝一件灰色的短褂,针脚细密,是给自卫队的百姓准备的。她抬头看了眼沈砚之,手里的针线没停:“昨天我去弄堂里送衣服,听到两个日军士兵在杂货店买东西,用军靴换了两双布鞋,说要寄回日本给家里人。还有个小士兵,偷偷问杂货铺老板‘能不能帮忙买张船票’,被旁边的军官骂了一顿,脸都白了。”
“士气散了,仗就打不下去了。”沈砚之走到窗边,撩开窗帘一角,看着外面的街道。几个穿黄军装的日军士兵背着枪走过,脚步拖沓,帽檐压得很低,没人像以前那样挺胸抬头地巡逻,反而时不时往弄堂里瞟,像是在找什么能换钱的东西——有个士兵甚至把腰间的刺刀解下来,偷偷递给卖烟的小贩,换了一包“哈德门”,揣在怀里飞快地走了。
这场景,和三年前他刚到上海时截然不同。那时候的日军,眼里带着占领者的嚣张,街头的百姓见了他们都要绕着走;可现在,连最普通的士兵都知道,“大东亚共荣”是自欺欺人,他们的家乡,或许早就被盟军的炸弹炸成了废墟。
就在这时,裁缝铺的门被轻轻推开,风铃响了一声。张彪探进头来,脸上沾着点面粉,手里拎着个油纸包:“沈同志,苏同志,刚从面包房买的,还热乎着。”他把油纸包放在桌上,压低声音,“刚才在特高课附近的杂货铺,听到松井的副官在打电话,说总部发来电报,让他们‘清点物资,做好回撤准备’,还提到‘本土资源耗尽,无法再支援上海’。”
沈砚之心里一紧:“回撤准备?松井是什么反应?”
“没看到人,但副官挂了电话后,脸色难看极了,还踢翻了门口的垃圾桶。”张彪拿起一个面包,掰了一半递给苏清媛,“我还听说,最近日军的粮仓开始限制供应,士兵们每天只能领到两顿粥,有几个新兵饿极了,晚上偷偷去老百姓的菜地里偷萝卜,被抓住后,军官也没严惩,只是骂了两句就放了——换以前,早被拉去关禁闭了。”
苏清媛咬了口面包,眼神变得严肃:“要是日本真的投降,上海的局势恐怕会更乱。汪伪政府的那些人,肯定会卷着钱逃跑;军统那边,说不定会趁机抢地盘;还有些汉奸,会想办法洗白自己,说不定会对老百姓下手。我们得提前准备,不能让局面失控。”
“没错。”沈砚之点头,“我已经让老枪联系陈峰了,约了明天在法租界的咖啡馆见面,一起商量对策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三件事:一是摸清日军在上海的军火库、粮仓和工厂位置,防止他们投降前狗急跳墙,把这些设施都烧了;二是组织老百姓成立自卫队,教他们用简单的武器保护自己,别让汉奸或者散兵欺负;三是和军统达成协议,投降后暂时共同管理上海,别因为抢地盘打起来,让老百姓遭殃。”
第二天上午,法租界的“蓝调咖啡馆”里,留声机放着舒缓的爵士乐,掩盖了角落里的谈话声。沈砚之和老枪坐在靠窗的位置,对面的陈峰穿着件深色西装,头发梳得整齐,只是眼底的红血丝暴露了他最近的忙碌——军统也收到了日本可能投降的消息,正在秘密部署,准备接收上海的部分机构。
“沈兄,你说的合作,我同意。”陈峰搅拌着咖啡,语气很直接,“但丑话说在前面,军统在上海经营多年,投降后,政府机关和重要的交通线,得归我们管。至于军火库和粮仓,可以一起清点,优先分给老百姓,这点没问题。”
“可以。”沈砚之没犹豫,“我们的目的不是抢地盘,是保护老百姓,维护上海的秩序。只要军统不伤害百姓,不破坏工厂,我们可以配合你们的工作。”
老枪在旁边补充:“还有,日军投降后,肯定会有散兵游勇到处作乱,我们可以分工——军统负责市区的主要街道和政府机关,我们负责弄堂和郊区的工厂,遇到问题,及时互通消息,别各自为战。”
陈峰点头,从怀里掏出一张纸,推到沈砚之面前:“这是军统掌握的部分日军设施位置,有三个军火库和两个粮仓,你们可以参考。至于江南造船厂,日军看得很紧,我们的人一直没机会靠近,你们有没有办法摸清里面的情况?”
沈砚之拿起纸,扫了一眼上面的地址,心里有了数:“江南造船厂的事,我让若涵去试试。她现在在中华书局工作,有个客户是造船厂的工程师,或许能从他嘴里套出点消息。”
约定好合作细节后,几人各自离开。沈砚之刚回到裁缝铺,就看到若涵坐在里间,手里拿着一本诗集,正是上次她被抓时,松井从她家里搜走又还回来的那本——其实里面夹着地下党的联络暗号,松井没发现,又还给了她。
“沈同志,你回来了。”若涵站起来,脸上带着点兴奋,“我刚才见到造船厂的刘工程师了,他说最近造船厂的日军管得特别严,每天都有卡车往里面运东西,晚上还能听到‘轰隆’的声音,像是在装炸药。刘工程师偷偷问过一个日本同事,那人说‘上面有命令,要是终战了,就把造船厂炸了,不能留给中国人’。”
“炸了造船厂?”沈砚之的脸色瞬间变了。江南造船厂是上海最大的工业设施,从清朝就开始建造,能生产轮船和机器,要是被炸毁,不仅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,还会影响战后中国的工业重建——松井这是想在投降前,给中国留下一个烂摊子!
“刘工程师还说,负责炸造船厂的,就是松井。”若涵的声音压低,“他看到松井上周去了造船厂,和那里的日军军官聊了很久,还指着造船厂的船坞,像是在布置任务。”
沈砚之握紧了拳头,心里又急又怒。他知道松井的性格,这人偏执又狠辣,要是真让他炸了造船厂,后果不堪设想。“若涵,你再想办法联系刘工程师,让他摸清炸药的存放位置和具体的爆破时间,越详细越好。记住,一定要小心,别被松井的人发现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若涵点头,把诗集放进包里,“我会以送书的名义,再去见刘工程师,不会引起怀疑。”
接下来的几天,上海的气氛越来越紧张。日军的巡逻次数明显增加,街头的布告栏上,贴满了“坚守大东亚共荣”的标语,可没人相信——连汪伪政府的官员,都开始偷偷把家人送到香港,家里的金银珠宝也一箱箱往外国银行运。
沈砚之和苏清媛则忙着组织自卫队。他们在上海的各个弄堂里奔走,先是找弄堂里有威望的老人,比如静安寺路的王大爷、浙江中路的李奶奶,跟他们说明情况,让他们带头组织百姓;然后又找了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,教他们用木棍、菜刀、铁锹做武器,还编了简单的口号:“护家园,防散兵,保平安!”
“沈同志,这木棍真能打跑坏人吗?”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叫小杨,手里握着一根磨得光滑的木棍,眼神里带着点怀疑。他的父亲去年被日军抓去做劳工,再也没回来,母亲身体不好,家里全靠他卖报纸为生。
沈砚之拍了拍他的肩膀:“能。要是遇到散兵或者汉奸,我们人多,一起上,他们肯定不敢怎么样。而且我们还有老枪同志,他会教我们怎么躲子弹,怎么用最简单的办法保护自己。”
老枪站在旁边,手里拿着一把缴获的日军刺刀,正在给百姓演示怎么用木棍格挡:“大家看好了,要是有人用刀砍过来,别慌,用木棍对着他的手腕打,只要他的刀掉了,就好办了。记住,不到万不得已,别主动伤人,我们的目的是保护自己,不是打架。”
百姓们围在一起,认真地学着。王大爷把家里的菜刀拿出来,用布条缠在刀柄上,说:“我虽然年纪大了,但要是真有坏人来弄堂里抢东西,我就用这把刀护着孙子,绝不让他们欺负!”
李奶奶则煮了一大锅绿豆汤,分给大家:“天热,大家喝点汤,别中暑了。咱们弄堂里的人,要团结在一起,才能平安度过这阵子。”
弄堂里的气氛,从一开始的恐惧和犹豫,慢慢变成了团结和期待。大家知道,日本投降是迟早的事,只要再坚持一阵子,就能过上安稳日子。
而此时的特高课办公室里,松井正坐在椅子上,手里拿着一张泛黄的照片——照片上是他年轻时在东京的合影,身边站着他的妻子和女儿,笑容灿烂。桌子上,放着总部发来的最后一封电报,上面用红色的字写着:“八月中旬,将有终战诏书,各部队做好投降准备,不得擅自抵抗。”
“终战……”松井低声念着这两个字,手指用力攥着照片,指甲都快嵌进肉里。他想起自己刚到上海时,意气风发,以为能为“大日本帝国”开拓疆土,可现在,却要带着“战败者”的身份回国,甚至可能被当成战犯审判——他不甘心!
“课长,炸药已经运到江南造船厂了,放在船坞的地下室里,一共两百箱,足够把整个造船厂炸平。”小林走进来,手里拿着一份清单,脸上带着点兴奋,“我们可以在八月十五日那天,等天皇宣布投降后,立刻引爆炸药,让中国人永远记住我们的厉害!”
松井抬起头,眼神里满是疯狂:“好!就这么办!江南造船厂是中国的工业命脉,炸了它,就算我们投降了,中国的工业发展也会倒退十年!这是我们最后的‘荣耀’,绝不能让它落空!”
小林点头,转身要走,却被松井叫住:“等等,你去把特高课的人都集合起来,告诉他们,八月十五日那天,除了留守的人,其他人都去造船厂,帮着布置炸药。要是有人敢违抗命令,军法处置!”
“是!课长!”小林敬了个礼,快步走了出去。
松井看着窗外,上海的天空灰蒙蒙的,像是要下雨。他知道,自己这么做,是在给自己找一条绝路,可他不愿意承认失败——他宁愿毁掉一切,也不愿意让中国人得到一丝好处。
而此时的沈砚之,已经通过若涵拿到了刘工程师传来的消息:炸药存放在江南造船厂船坞的地下室,爆破时间定在八月十五日中午十二点,也就是天皇宣布投降后的一小时。松井会亲自带队去布置炸药,特高课的大部分人都会跟着去。
“十二点……”沈砚之看着手里的地图,上面用红笔标出了地下室的位置和日军的守卫情况,“我们只有不到十天的时间了。老枪,你带几个身手好的同志,潜入造船厂,想办法破坏炸药的引线;陈峰,你联系军统的人,在八月十五日那天,牵制松井的部队,别让他们靠近地下室;清媛,你组织自卫队,在造船厂附近的弄堂里待命,要是有日军散兵逃跑,帮忙拦截;若涵,你继续和刘工程师保持联系,随时关注松井的动向。”
“没问题!”老枪拍了拍胸脯,“我以前在部队里学过拆炸弹,只要能靠近地下室,一定能破坏引线。”
陈峰也点头:“军统会派五十个人,在造船厂门口埋伏,松井的人一到,我们就开枪吸引他们的注意力,给老枪争取时间。”
苏清媛和若涵也表示会做好自己的任务。几人围在地图前,商量着每一个细节,确保没有遗漏——他们知道,这是日本投降前的最后一场战斗,不仅要阻止松井炸毁造船厂,还要保护好上海的百姓,让这座被占领了八年的城市,能平安地迎来解放。
八月十日那天,上海下起了小雨,淅淅沥沥的,把街头的灰尘都洗干净了。沈砚之站在裁缝铺的门口,看着弄堂里的百姓在练习自卫动作,王大爷正教小杨怎么用菜刀格挡,李奶奶在给大家煮姜汤,心里突然觉得很踏实。
他想起三年前刚到上海时,老顾在“一品香”茶馆里跟他说的话:“我们做这些,不是为了自己,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安稳日子,能让孩子们不用再躲炸弹,能让这座城市,重新变得有生气。”
现在,这个日子,终于要来了。
只是他没想到,松井的疯狂,比他想象的还要可怕——就在八月十二日晚上,地下党的线人突然传来消息:松井提前了爆破时间,定在八月十四日晚上八点,而且还加派了兵力,守住造船厂的各个出口,不让任何人靠近。
“提前了?”沈砚之看着消息,心里一紧,“看来松井是怕夜长梦多,想在投降前赶紧动手。我们得调整计划,今晚就行动!”